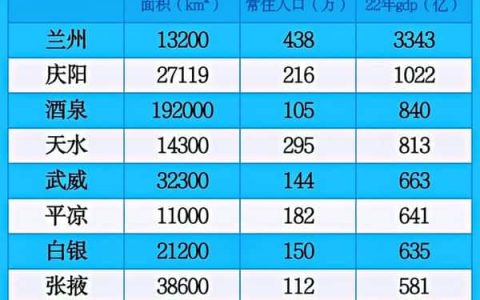·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就算你是完美的,这个世界却不是。
人的泪腺随时都在分泌眼泪,眼泪可以起到湿润角膜,润滑眼球的作用。如果不慎过分靠近遇刺的洋葱,泪腺分泌眼泪的速度就会大大地增加。如果眼眶容纳不下,眼泪就会流出来。
有一类人,因为曾过分靠近遇刺的洋人,也会导致自身泪腺分泌眼泪的速度大大地增加。如果此时你是在厕所里,“哭晕也就哭晕了吧”,但若不幸在直播节目,你的那一滴泪,就需要如实交代除了无机盐、蛋白质、溶菌酶、免疫球蛋白A,是否还含有其它阶级成分。
当联大皆茶馆的茶友们都以为笨鸟这期茶话是要科普泪腺时,那可真是高看笨鸟了,俺只能简单说说这《一滴泪》(A Single Tear)。

《一滴泪》A Single Tear
《一滴泪》的作者巫宁坤是个爱笑的人,他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授时的研究生郭中迅在毕业三十年后仍然清楚记得巫宁坤授课时的样子,戴着厚眼镜,站在黑板前,头发凌乱,看起来有些“狂气”:“巫先生一张嘴,声音很大,笑声也大。”
《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在美国采访巫宁坤时是这样说的:“ 巫宁坤先生住在华盛顿郊区的国际公寓,家中摆设简朴而富有文化气息。书桌上引人注目的是余英时、巫宁坤、乔志高三人并肩大笑的照片。交谈了一会儿,我发现巫先生有一个特点:几乎每讲完一句话都会笑。”
生活中喜欢大笑的巫宁坤更喜欢提自己大哭的“当年勇”。他在《漫天烽火忘年情》一文中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冬,侵华日军已经从上海沿沪宁路直迫首都南京,我的家乡扬州也岌岌可危。我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从初一起一直在省立扬州中学就读,当时正上高二。十一月中旬,学校奉命解散,全校师生集聚树人堂,唱起《松花江上》,泣不成声,随即纷纷离校,各谋生路。”
在徐蓓执导的反映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里,总共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学者出场。继《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首发出场后,影片画面依次出现扬州的廋西湖、扬州彩衣街,此时的画外音里传来巫宁坤著名的笑声,当镜头转向巫宁坤回忆当年学校解散时同学们齐唱《松花江上》的场景时,却又见他一度哽咽停顿后,坚持用哭腔演绎了《松花江上》。


我是扬州人,我们都唱《松花江上》
巫宁坤1920年9月出生在扬州。1936年春天,江苏省教育厅组织几所中学的学生到镇江集中军训,扬州中学的巫宁坤、江阴南箐中学的汪曾祺,还有苏州中学的赵全章三人编在一个中队。他们年龄相仿,气味相投,很快便成了好朋友。1939年,他们仨都是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又一同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只不过汪曾祺去了中文系,巫宁坤和赵全章读了外文系。
1984年汪曾祺在《泡茶馆》中这样写道:“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汪曾祺文中提到的“两个外文系同学”就是巫宁坤和赵全章。
2008年巫宁坤在香港《大公报》上也写过《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一文回忆往事:每天课后,我们仨就各自带上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去泡茶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边看书,多半是课外读物,或写点儿什么东西。茶馆就是我们的“书斋”。谁写好一篇东西,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说的文采就让我俩叹服。全章中英文都好,经常写抒情小诗,后来一篇接一篇从英文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也写一些小东西。我们最初的习作都是在这家茶馆里泡出来的,投给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诗小文都陆续注销(笨鸟注:原文如此,不知何意,盼有解读者指点)来了。经常饥肠辘辘的穷学生,谁一拿到稿费我们仨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
“打牙祭”的生活很快就被“打日本”替代了,巫宁坤在西南联大读了不到两年书,即在1941年中止学业,为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担任翻译。太平洋战争以后,中国空军师的飞行人员被送到美国去学习。1943年12月,巫宁坤作为翻译也随同前往美国。仗打完后,巫宁坤留在了美国继续读书,并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1951年他在读博士时,不断收到来自国内朋友的来信让他回国。
先是妹妹来信,然后是他的西南联大同学、巴金的夫人萧珊来信,最终促成巫宁坤终止博士学业提前回国的是时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的赵萝蕤,正是她报请当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电聘巫宁坤回国执教的,也是她在1951年8月到北京火车站亲自迎接了满面笑容的巫宁坤。这“一滴泪”就是从巫宁坤归来那一天开始与“泪腺组织”达成了协议:不受难不流淌。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交代,1951年7月,巫宁坤在旧金山临回国前是李政道亲自帮他打包行李,并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巫宁坤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还前来送行道别,巫宁坤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此处的“一笑”按照巫宁坤的风格应该也是“大笑”。
回国不到一年,巫宁坤就笑不出来了。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合并,他所在的有教会学校背景的北京燕京大学不存在了,西语系五个教授中只有他被分配到了天津南开大学,向他宣布这个消息的赵萝蕤当场就忍不住大哭起来。当事人巫宁坤倒是没有那么伤心,他在日后回忆赵萝蕤的文章中写道: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以四海为家的巫宁坤想不到南开大学居然有一个比他小11岁的外语系大三女学生在那里等着与他组建家庭。出身于富商家庭的李怡楷,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5岁那年李怡楷也受洗了。李怡楷对这个曾经参军、留学、学识渊博、又会大笑的巫教授颇为倾心,巫宁坤也对这个女生颇有好感。1954年7月,李怡楷一毕业,两人就奔了教堂找神父主持仪式了。

两束芦苇,互倚不倒
天主保佑了巫宁坤,后面发生的事情证明如果不是这段神奇的姻缘,巫宁坤一定活不到1979年李政道访华时与他重聚的那一天。李政道比巫宁坤小六岁,成熟度却比巫宁坤大六岁。1950年6月,李政道心仪的姑娘秦惠?从圣玛丽学院刚毕业,他们就在芝加哥市政厅登记结了婚。巧的是,秦惠?也信教,出自上海的天主教名门望族家庭。这也许是受父亲影响,李政道的父亲李骏康娶的是天主教名门世家张明璋。
在选择伴侣方面,巫宁坤和李政道走了相似的一条道路,但是1957年成了两个人人生道路的分水岭,那一年李政道在瑞典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巫宁坤则成了极右分子,要被劳动教养。在被送往著名的半步桥监狱看守所的前一天,李怡楷拉着巫宁坤的手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每日每夜为你祈祷,坚守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坚守对生活的信念。天主保佑!”
天主是这样保佑巫宁坤的,他先被调至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在那边受苦受难,后又被转到位于唐山与天津之间的清河农场继续受苦受难。巫宁坤因为长期缺食少粮全身浮肿差点死在了清河农场。李怡楷的二哥曾带着吃的东西来清河农场探访巫宁坤,他居然强行把二舅哥回去路上吃的干粮也“打劫”留下了。终于有一天,巫宁坤写信给妻子李怡楷,说自己已经浮肿多天了,生命将会不久于人世,可能这是最后一面了。来吧,快带着女儿来看我吧。
李怡楷望着行走在死亡边缘的夫君,决定开始她的救夫计划。她开始去北京,找到国际关系学院的校长,陈述求情,最后终于打动了校长,以学校缺乏称职的教授为由,让巫宁坤保外就医。李怡楷之所以拼死也要把夫君救出来,是因为在清河农场她碰到过一个小学教师的妻子带着九岁的儿子,来为爱人收尸。
1979年5月巫宁坤奉命从安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看到报纸上登载李政道访华讲学的消息,便赶到北京饭店的国宾馆看望自己的老同学。临别时,他突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他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换句话说,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国政府的国宾?
谁都知道这个奇想的答案,联大皆茶馆的茶友们就别说出来了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991年巫宁坤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退休后定居在美国。1993年,他用英文写成的自传小说《一滴泪》在美国出版了。其中所讲述的“文革”受难史,轰动西方世界。换来的代价是,巫宁坤的房子被国家收回去了,夫妇俩的退休金也被停发了。

没有退休金但还拥有彼此
在巫宁坤回忆赵萝蕤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九三年九月,萝蕤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去讲学两周。九月二十四日,她从中大写信到美国给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过年初在纽约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我还在为你的书而感到振奋。”又说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书,“我说不但内容一字动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动不得。”同时,她也知道这本纪实作品,虽然平实之极,却已经使我们陷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的境地。在信的结尾,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发出深情的邀请︰“你和怡楷来京可住我处,我们现在西屋作客房,有全套卫生设备。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饭。”
联大皆茶馆的茶友应该还能记得前几期笨鸟在写陈梦家和赵萝蕤时,提过上海博物馆曾经收藏了一批陈梦家的明式家具。2005年,巫宁坤回国探亲访友,曾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馆,专程参观陈梦家先生生前搜集的明代家具精品,凭吊两位故人。
2019年8月10日,巫宁坤在美国去世的消息在国内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看过他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可能不少,但是读过《一滴泪》的人应该屈指可数。巫宁坤对于“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的人生并不悔恨,他对《甲骨》作者何伟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于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一滴泪》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许渊冲是认可巫宁坤的英语水准的,但是他要强调一点,巫宁坤的法语不如他。许渊冲在翻译界备受争议的一点是他过分强调了意译。1995年他发起了《红与黑》的翻译论战,认为翻译应该是意译而非直译。这其实是一场翻译界关于“真”与“美”的选择。
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全书的最后一句话“Elle mourut”,杨苡的先生、翻译家赵瑞蕻译成“她死了”,许渊冲译成“魂归离恨天”。翻译家冯亦代形容许渊冲的翻译是“花花绿绿的东西”:“原文就是‘她死了’”。但在许渊冲看来,市长夫人是含恨而死:“要表示含恨而死,还有比‘魂归离恨天’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吗?”许渊冲不服。
“文革”期间,许渊冲因为翻译毛泽东的那句“不爱红装爱武装”采用了“意译”而被红卫兵用树枝抽了“一百鞭子”在他的屁股上,但是今天他依然喜欢把自己对这句诗的翻译当做得意之作。他把“红装”翻译成“power the face”,“武装”则是“face the powder”,巧妙运用了两个英文单词的不同意思,这让他很是得意。而当年那用树枝抽的一百鞭子,以及事后为了继续翻译只能坐在救生圈上的事情,他自己倒是提都不提了。
如今,曾经和许渊冲论战的诸多翻译家包括活了一百岁的许渊冲自己都已经离世,但关于“真”与“美”的争论却并未停歇。类似的争论在东洋人遇刺之事上同样掀起了一阵波澜,经常光顾联大皆茶馆的茶友们绝不会简单地将此事分为“哭晕派”和“吃席派”来站队。一个九零后,看过《九零后》后,应该也不会头脑简单地站队,而是学会了在“死了”和“魂归”之间斟酌词汇。
笨鸟始终认为一个灵魂受难者发出的笑声是最动听的。巫宁坤的女儿巫一毛在家里有时候就说自己的爹,为什么要回国,受这么多的苦。巫宁坤就会说,我要是不回去,就碰不到你妈,就没有你了,哈哈!

哈哈!

我归来、我受难、手幸存
本文内容源自网友投稿,多成号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不拥有所有权。如有侵权,请联系站长删除。qq97伍4伍0叁11